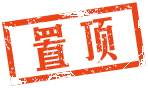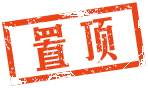(17)
九月的秋阳依旧栗烈,日光炙烤着红白跑道,草壤和汗液都在滋滋作响。
可是这阳光不会晒着郑总分毫。
在他的身侧,四十来岁的教授亲自为他打着伞。那中年男人比郑云龙矮上许多,此刻却微微弯下腰,伸直了胳膊掂着伞柄,做出一副谦恭的模样。
黑色阴影遮挡住毒辣的日头,他说这燥热的地面烫了郑总的鞋底,一个劲地要把人往学院办公室里请。
东林大学的校长撑着伞走在他们前面,一边引路,一边为郑云龙介绍各学院的人文风貌。右手边,一名女青年教师作陪,漫不经心地附和几句,就不再搭理他们。
一行人站在操场边,学生跑步经过时都向他们礼貌问好。校长挺欣慰,说学校的学风建设还算当得起校训“高风亮节,笃实博雅”。
一旁,教授笑眯眯应和着:“多亏了校长您躬身实践,为学生们做好榜样啊!”
他扭头一看,见郑总目光放空盯着远处,又捧上一句:“郑总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,学生们都特别仰慕您。这回您能出席运动会开幕式,我们倍感荣幸,倍感荣幸。”
那女导师斜睨了教授一眼,郑云龙听见她轻轻哼了一声。
郑云龙对学界的事情所知不多,但是东林大学这位物理学教授他倒是在媒体上见过。刘教授几次猥亵学生,男男女女都遭受过他的性骚扰。去年一个女学生因此自杀,事情闹大了。校方出了批文调查,却收集不到什么实证。后来新闻热度一降,不了了之了。
这类恭维的话听得郑云龙耳朵起茧,点点头敷衍他了事,一双眼睛瞅着站在操场另一端的人影。
那个男孩拎着个帆布包,静静地站在人群里,仰头盯着如洗的碧空。拉拉队的加油声此起彼伏,他却与周遭的热闹隔离,伫立的姿态像一棵寻找飞鸟的树。
郑云龙倒是没想到,能在东林大学遇见阿云嘎。
这实在是意外之喜。
郑氏集团虽私底下做着上海赌场的生意,明面上依然是正儿八经的珠宝企业,每年坚持向社会各界捐款,钱财大笔地支给社会公益,帮扶各大高校开展学生活动。这倒不是出自商人的良心,而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,以达财路亨通。
郑云龙此来是受了校方呈递的邀请,为秋季运动会的开幕式做个发起人。他也不是空手而来,运动会的一应器材全由郑氏集团采办,提供的奖品总价值千万,算是企业冠名运动会,一早就出了新闻校讯。
但这事对于声名赫赫的郑氏集团来说,实在只能算是芝麻大点的小事。校方也没料到郑云龙会亲自过来,自然给足了排面。这不,开幕式过后,校长就亲自陪同他参观校区。
此刻见郑总望着操场对面出神,一行人琢磨不透他在想什么。刚好两千米拉力赛的哨声响起,教授便随意捡些话题来暖场,不外乎夸赞学生们体魄强健,有毅力恒心,以后必是社会人才,也好入郑氏集团工作。
“我能去操场对面看看吗?”郑云龙问。
“当然可以,请。”校长说。
“我给您带路。”教授径直拆了跑道边的围挡带,领着他穿越跑道到对面去,丝毫不顾身后即将跑近了的选手。
看台上的学生们看见一行人突然走过来,目光一转,也不盯着在跑道上赛跑的选手了。
学生们礼貌地向老师们问好,纷纷打量起郑云龙来。
方才,郑云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讲话,学生们挨挨挤挤地坐在毫无遮挡物的草坪上熬时间,烈日底下谁都不愿抬头看。
如今,高挑的帅哥站在跟前,年轻俊逸,贵气逼人,扣到领子的衬衫纽扣又衬得他禁欲不可亵玩。这实在不是大学里那帮初谙世事的男孩们能比肩的。
一时间,看台上的赞叹声不绝于耳,男男女女都拿起手机对着郑云龙一阵猛拍,有的甚至发出几声痴笑来,大喊:“帅哥总裁,加个联系方式呗——”
校长思想保守,见这无礼的场面,面上挂不住,侧目去瞧郑云龙的脸色,有些尴尬。
郑云龙没理会这些。他兀自盯着不起眼的角落,眼里只有阿云嘎一个。耳边鼎沸的声音自动过滤出去,他仿佛能听见阿云嘎喉结一滑,咽口水的响动。
阿云嘎今日穿了一件橘色的短袖,下身是浅绿色的短裤衩,活像一只胡萝卜。他与郑云龙对视。
郑总冲他勾勾手,表情严肃认真,无声地动着嘴皮。
口型是:“过来,小胡萝卜。”
学生们不知道他在跟谁比划,只见阿云嘎穿越人海走下来,站到郑云龙跟前。他的一双腿修长笔直,站在郑总身边也只比他矮上三公分,竟没被比下去。
俩人站在一起养眼极了。
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讨论声。
“你说阿云嘎跟帅哥总裁什么关系?”
“长那么像,会不会是兄弟?”
“怎么可能!阿云嘎要是有这样的哥哥,哪用得着出去打工?”
“难不成……姓郑的是包养他的金主?”
“我靠,斯文败类?衣冠禽兽?”
只见那已经走下台去的人一转身,与窃窃私语的女孩们对视。
他的目光很平静,但那两盏眼睛里分明盘踞着一条毒蛇,嘶嘶地吐着信子,是盯住猎物的眼神。
她们立刻把嘴闭上了,尴尬地扭开脑袋,坐得直直的。
然而,阿云嘎什么也没说。他弯弯眉眼,什么都没听见似的,重新变回一只温驯无害的兔子,好像方才冰冷的眼神都是错觉。他路过女孩们,将座位上的东西拎起来,一拍脑袋,懊恼道:“哎呀,我忘了拿帆布包。”
阿云嘎拎着包走回郑云龙身边,也不开口说话,只拘谨地站着。郑云龙伸手捏捏他的脸颊,说:“瘦了你。”
那教授见二人很熟的样子,把阿云嘎往身边一带,故作亲热地搂住他的肩膀,手掌捏捏他的胳膊,问道:“郑总认识嘎子?”
阿云嘎眉头一颦,默默从教授怀里挣脱出来,与他拉开了点距离,站到郑云龙身后。
郑云龙咀嚼了一下“嘎子”两个字,回道:“嘎子是我认识的弟弟。”
教授听这意思,寻思他们不是表兄弟,但既然认识也值得吹捧,笑呵呵夸他:“嘎子是我们物理学院的学生,成绩挺好,是个顶顶聪明的孩子。”
阿云嘎没搭腔。郑云龙的心底里滋生出一丝莫名的骄傲来,如同家长听见老师夸奖自己的孩子。
他伸手揉揉阿云嘎的后脑勺,把那柔顺的头发撸得乱糟糟。阿云嘎盯着地,神色淡淡的。
郑云龙一心想与阿云嘎独处,便请校长一行人不用再跟着了,他就在这儿随意坐坐,有事打电话。校长起初坚持要陪,见他执拗,也不再推拒,指指旁边空荡荡的教师看台,告诉郑云龙可以坐那儿观看,不拥挤。
郑云龙便自然而然握住阿云嘎的手腕,一路牵着,将他带去教师看台。
学生们坐在两侧的看台上摩肩接踵,正中央高起的教师看台却空无一人。
阶梯状的台面堆满了灰尘,直接坐下去只怕会弄脏衣裤。郑云龙正要掏出口袋里的绢布擦干净两个人的位置,阿云嘎已从包里抽出了一沓湿巾,弯下腰仔细擦拭起来。
这场景,郑云龙见了多回了。
在勾栏里,阿云嘎也是这样,总是用抹布和湿巾为他擦净衬衫、皮鞋、脖子上的酒液。
那时,郑云龙是花了钱的顾客,阿云嘎是会所的侍从,这般服务他受得心安理得。如今站在学校里,郑云龙见他仍然这样,心里不是滋味。
可到底哪儿不对,他也说不出来,明明自己是受惯了他人侍奉的人,却觉得这些微末的事情该由自己来做。
郑云龙伸手拿过那团湿巾,说道:“我来吧。”
台面已被阿云嘎擦得很干净,郑云龙却捏着纸再抹了一遍。湿巾上裹的灰尘被他抖落下一些,反而没刚才干净了。
阿云嘎也不在乎,歪着头看他擦完,就拉着郑云龙坐下来。
看台顶上有遮挡棚顶,阴影之下倒是凉快许多。
他们并肩坐着,目光向下看。
炽烈的阳光下,人头攒动,加油声和哨声此起彼伏。学生们穿着各色衣裳,站在草坪上如一簇簇鲜艳的野花。
空气里混杂着塑胶跑道和汗液的气味,郑云龙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看看校园里的风景,闻闻这燃烧的青春的味道了。
明明他才二十九岁,可这情景仿佛尘封在遥远的过去,与淋漓鲜血一同埋葬起来,再也回不去了。
阿云嘎不问郑云龙为什么来这里,又是怎样找到他的,他只静静地陪他坐着,回忆那阵来自过去的风。
过了一会儿,郑云龙问他:“今年读大几?”
“大二。”阿云嘎答道。
他们之间好像很熟,熟到能在包厢里随时拥吻,可郑云龙连阿云嘎读大几都不知道。
哦,比他小九岁。
郑云龙瞅瞅身边的人,瞧见他浅绿色短裤底下一截白嫩的大腿根,如同贝壳肉被吞食后残留在壳内的那一丝贝柱。
郑云龙这样吃惯了珍馐的人,却偏爱这轻易舔不下来的白肉。他舔了舔嘴唇。
阿云嘎,你怎么能这样坦然地坐在我身边呢?
你怎么能毫无防备呢?
郑云龙有时候将阿云嘎当做一只偶然飞入他世界里的来自春天的鸟,爆裂在他脑海里的一颗香甜的爆米花。
可他自己也明白,他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想啃食阿云嘎,像一只吸血鬼一样,用牙齿扎破他的血管,咬上他的大腿根,吸干他的全部活力,拆出他的肋骨挂在家里的墙壁上。
郑云龙盼着黑夜来临,他能拽住阿云嘎说:跟我一起迈入肮脏的永夜吧。
这念头一晃而过,他不想惊走这只小鹦鹉。将那些贪婪的欲望藏匿起来,郑云龙衣冠整齐地坐在他身边,目光悄悄揉过他丰润的大腿根,又一次把心底的火焰吹熄。
他正想着,一支棒棒糖递在了郑云龙面前,是阿云嘎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的。
那颗糖是橙子的形状,小巧玲珑的,用透明的糖纸包着,连着一根细长的柄。
郑云龙接过来,看着阿云嘎又从包里拿出一支西瓜形状的,拆了糖纸放进嘴里。
他舔了舔又拿出来,举在郑云龙面前展示。
小西瓜薄薄的,晶莹剔透。
“郑总,吃糖。”阿云嘎弯弯眼睛,示意他手里的那颗小橙子,笑得像轻云一样。
郑云龙看着他的眼睛出神,话在脑子里转了一圈,就变了样。他一伸手接过那支西瓜味的,把那颗被舔湿了的糖果放进嘴里,舌头包裹着硬糖的边缘,细细地尝。
甜津津的,他的一颗心沁入了甘甜的西瓜汁。
阿云嘎看着他将那颗糖来回舔舐,喉结动了动,故作漫不经心,又从包里拿出一支西瓜味的,拆了包装默默地吃着。
郑总受了这一颗糖的恩惠,歪过脑袋问他:“最近还好吗?”
郑云龙自从陪阿云嘎一起去看了场电影,就忙着处理赌场的事情,很久没去勾栏找他。
“挺好的。”阿云嘎把糖果拿出来,捏着长柄的底端晃悠那颗糖。
郑云龙瞟他一眼,道:“有人欺负你了,就来告诉我,知道吧。”
那颗小西瓜不晃了。
阿云嘎说:“郑总有什么烦心事了,也可以来告诉我。”
郑云龙扭头,见他说得很认真,笑笑,不置可否。
(18)
坐了一会儿,阿云嘎扯着郑云龙下去掷飞镖。那是操场西北角的一块空地,三张课桌拼起来,被人群围满。
对面五米处放置着三面标靶,这是学校另设的游戏项目。
郑云龙问他:“怎么想玩这个?”
阿云嘎指指桌子旁堆放的奖品,说:“想赢奖品。”
桌面上摆了两台笔记本电脑,也有保温杯、笔记本这类生活、学习用品,都是郑氏集团采办的奖品。
郑云龙陪着阿云嘎排在长长的队列后边儿,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悻悻而归,怕等了许久之后,阿云嘎投掷不中,心里失望。郑云龙便拍拍阿云嘎的肩膀,对他说:“投不中也没关系,回头我买给你。”
这话一落地,倒真像是金主包养的关系了。郑云龙说完就有些后悔,身边的人却歪头笑笑:“我想把赢来的东西送给郑总的。”
郑云龙纳闷,他要送他什么?疑惑时,队伍已排到了。
五次机会,靠分数兑奖。阿云嘎拿起桌上的五枚黄铜飞镖,看了眼靶子上的数字所对应的奖品。随及三指握镖,右脚在前,肩与飞镖盘呈九十度。
郑云龙看他的模样,就知道他是很会的。
阿云嘎看着靶心。郑云龙看着阿云嘎。
他拔肩站立,一双眼睛里尽显凌厉的锋芒,剑拔弩张的样子与往日大不相同。郑云龙觑见他这等勃发的英姿,喜爱之心更甚。
原来他的小鹦鹉,也能有这样的一面。
“唰。”
飞镖破风而出,郑云龙扭头去看,却见那枚镖划了一个抛物线,直跌在地上。
靶子都没碰到。
郑云龙说:“不急不急,镖针朝上掷,用五指握镖也行,加速时能控制得更好。”
阿云嘎点点头,凝神盯着那面标靶,拿起第二支镖。
气势很足,飞镖“嗖”地掷出去,擦着标靶的边过去,依旧砸在地上。
郑云龙给他捧场:“不错,擦着靶了。”
第三支、第四支堪堪落在靶子的边沿位置,郑云龙见那镖针的位置朝下,飞得毫无章法,轨迹颇为刁钻,心想,他之前的气势只怕都是虚的。
阿云嘎拿起第五支镖时,郑云龙已经不抱希望了,轻轻说了句“瞄准”,盘算着过两天送几十台笔记本电脑去勾栏,权当做常客的赠礼。
他抬起头,却见那支镖稳稳地扎在靶上,不是靶中央,很边缘的位置。郑云龙挺意外,夸了一句“真棒”,抬头去瞧那兑奖单。
三十六分的区域,一台电子分析天平。
阿云嘎从主持人那儿接过那台仪器,从人群中挤出来时笑得挺开心。
郑云龙用指关节敲敲包装盒:“喜欢这个?”
阿云嘎摇摇头,用指甲划开胶带封口,笑着说:“我想送给郑总这个。”
他从里面拎出一颗银色柱体,放进郑云龙的手心里。
那是一枚金属砝码。郑云龙颠了颠,用两根手指拨拉着观察,不明所以。
阿云嘎盯着他的掌心,问他:“郑总还记得雏鹰小学吗?”
郑云龙很懵:“什么,雏鹰…小学?
“十一年前我们在那儿见过一面。郑总大概不记得了。那会儿我才小学二年级,还是个小孩儿,”他笑笑,“郑总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。”
郑云龙试图从记忆的边角料中裁剪出当年的回忆。他知道,他高中刚毕业时,去过一所希望小学支教,大概一个月的时间。是叫雏鹰小学吗?
“你在那儿念过书?”他好奇道。
“嗯,”阿云嘎看着他的眼睛,说:“当时你也给过我一颗砝码。”
郑云龙不记得了。
他在看不见的刀锋上行走太久,心里头剩不了多少往日回忆。站在权力的最中心,那些旮旯里的故事早被他弄丢了。
在那所乡镇边缘的希望小学,孤弱的孩子们每日都承受着校园欺凌。父母远走他乡,老师们日日为生计苦熬,没人呵护着,就只能在鄙夷的脏水洼中辗转求活。
十一年前的夏天,九岁的阿云嘎还不如立式风扇高,被一帮高年级的男孩子追打着逃到操场。郑云龙当时正在操场的风口抽烟,见这以多欺少的场景,二话不说护住他。
那年轻小伙带他回办公室,为他满是伤口的手臂涂药,要他受了欺负就来跟老师说。后来,郑云龙还时不时捎给他一些城里才有的吃食,在无人角落里教他几句歌。
在希望小学里,最难得一见的就是希望。
郑云龙临走时,往阿云嘎手心里放了一颗砝码。
他说:“强大起来,你得为自己加码。”
身后因中镖而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,生命的静流在喧嚣中是微不足道的。阿云嘎在郑云龙眼睛里寻见一片茫然,倒也不执着于让他想起那些被灰尘吞没了的往事。
那颗砝码被阳光兜出一方矮矮的阴影,他们俩站得很近,两只长长的人影贴合在一起,如一对暂时的恋人。
阿云嘎轻轻说:“郑总,往后我就是你的砝码。”
这许诺被鼎沸的人声淹没,郑云龙不知道他说了什么,只是伸手揉揉他的脑袋,将这新奇的小物件放进上衣口袋里。
定情信物吗?郑云龙用手指捏着那颗砝码,忍不住想。
(19)
喇叭声在此刻响起,裁判员朗声播报着今天下午的比赛项目。郑云龙看了一眼手表,两点。
阿云嘎听完那一通广播,说:“郑总,再过两个小时,我就要去参加标枪比赛啦。得先回寝室拿号码牌,顺便把天平放回去。”
“你还会标枪?”
“当然啦!”
他点点头说:“好,那我自己逛逛。一会儿只怕等不到看你比赛,我就得先走了。”
阿云嘎冲他一笑,也不说再见,端着天平走了。
郑云龙一个人在校区里头闲逛,分针转悠转悠。
快到三点时,他把手伸进服帖的西装口袋里,捏住那枚信封,兴奋地摩挲了两下。
分针“咔哒”一声,指向“12”,手机铃应声而起。
G:实验楼旁的器材室。摄像头已经锁定了画面,三点二十分解锁,速度要快。